“在目睹了众多艺术现场的失望时刻后,才让我意识到我们的艺术有时候离现实太远,才让我想要去知道艺术在成为艺术之前的潜能是什么,我是在大把大把远离艺术的时间里,才发现当代民间现场是一个可以观察当代中国和某些切身问题的入口。”
2024年,策展人、研究者王欢在MACA美凯龙艺术中心策划了主题群展“民间自有序”,作为长期研究项目“秘密社会与艺术自驱力” (始于2021年) 的重要组成部份,展览围绕“从民间的创造冲动和自我秩序中我们能看到什么?如果要进行一个艺术式的提问又应该指向何处?”这一问题,重新对“民间”在此时此刻的可能性展开讨论。
讨论“民间”的切入点有许多,例如:民俗的民间、民艺的民间以及与政权呈对峙状态的民间等等。就艺术领域而言,从曾在传统艺术史叙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精英-民间”二元对立,到1919年后“民间”与“人民”概念范畴的转变,再到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于人民艺术提出新的要求,“民间”的定义日益复杂化。及至1980年至1990年代,“气功热”席卷全国,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另类“民间”,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草创阶段,部分中国早期前卫艺术的重要实践者在创作中大量援引中国本土的、民间的传统因素。及至2003年,由“长征计划”发起的“民间的力量”系列展览,首次呈现了“非职业”艺术家群体的艺术创作,其策展企图即是“以各个艺术家各自自学成才的技艺所展开的丰富叙事,扭转这个有高度排他性的文化生产状况”,其中就有日后广为人知的郭凤怡。尽管如此,直到郭凤怡参与2017年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其作为艺术家的身份依然备受质疑,甚至引发了彼时艺术世界的论争。
2019年后,由疫情引发的对于不确定未来的普遍担忧,或许变相促成了神秘主义民间的回潮。那么,在2025年的现实语境中,我们再次强调“民间”的特殊性体现在哪里?为此,我们邀请王欢围绕其“民间”研究的出发点、不同时代的个体 (无论是艺术家还是非艺术家) 回应“民间”的方式、研究型展览/研究性艺术与“真问题”的提出,以及民间的潜力中蕴藏的革命与暴力等方面与我们进行了分享。

策展人、研究者王欢
Art-Ba-Ba:
“民间”和“民间艺术”的概念都有着自身的发展过程,从2003年长征计划六个阶段的“民间的力量”系列展览,到近年当代艺术中包括神秘性、生态、地方性种种新的语境中的“民间”,你怎么看艺术界与民间之间的发展和变化?
王 欢:
首先,我提议我们能否先不要把“民间艺术”视为某种区别于“当代艺术”的艺术类型?如果此刻我们谈论的是中国语境,在我的观点里,那个姑且被我们称之为民间艺术的词,很可能背后牵连着太多长久以来埋藏过深的儒释道价值观和被叠加的历史条件,甚至可以说它是某种“中国式思想”的外化物。“民间经验”是一个非常具有“底色”意味的思想遗产。所以,如果回顾中国的当代艺术道路与“民间”的关系,我会倾向于回溯到上世纪80、90年代的创作,彼时的艺术家们在面临尚且陌生的“当代艺术”概念时,多少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来自中国本土的思想进行创作。我们才得以看到像黄永砯、蔡国强、吕胜中等等这些著名的名字们其创作的“底色”,这是本土经验与陌生经验发生摩擦且大家必须要在这种摩擦中有效工作的时代。


黄永砯,《世界剧场》,1993年
金属、木头、暖灯、电线、昆虫、爬行动物

吕胜中,《替身》 ,1995年
装置,行为
“亚洲第四届美术展”,东京世田谷美术馆

蔡国强,《撞墙》,2006
99只真实大小的狼复制品、玻璃墙;狼:混凝紙糊、石膏、玻璃纤维、树脂和绘制毛皮,尺寸可变
如果一定要将其整合进整个当代艺术世界并标记一个坐标,的确从表面上看,借用传统中国的思想或许是面对新的艺术语境时某种中国主体性的体现,抑或被解读为一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抵抗,我觉得这有本能反映的意味。
但是,我认为重要的从来不是中国艺术家如何把自己“合法”地嵌入到西方语境的问题,而是说我们能不能放大一个尺度,平等地看待东方西方的“划分”。众所周知,艺术史从现代主义走到观念艺术,又经历后现代的转向,到如今的当代艺术,其实艺术的语境从来不是被建构出来的一个一成不变的对象,而是由历代的实践者们通过自身的创作不断地定义艺术是什么。我们目睹过太多曾经不被认为是艺术的,会因为“艺术的条件”改变而被认为是艺术,同理,曾经被认为是主流艺术的也很可能会变得边缘。我非常谨慎地看待艺术定义与分类这件事情。
回到“长征计划”的时间线,2003年前后的中国艺术生态还处于建设初期,即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长征计划毫无疑问也是一个非常有先见性的艺术行动,它几乎起到了某种艺术概念和认知的纠正性意义。除此之外,还有2005年由吕胜中担任系主任的央美实验艺术系其前身就是民间美术系,将传统工艺和民俗的田野考察作为艺术教育的必要实践方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90年代还是2000年以来,不同实践者各自引用的“民间”,其所遭遇的社会现场与艺术现场显然是不一样的。

“长征空间 — 民间的力量”展览现场,2003年
第一阶段|郭凤怡、蒋济渭、李天炳、王文海
图片来自于长征计划

延安革命纪念馆退休讲解员“延安泥塑王”王文海、来自闽西老革命根据地山村的吉尼斯纪录保持者“天光摄影师”李天炳与现场观众观看郭凤怡现场作画,2003年
图片来自于长征计划
Art-Ba-Ba:
这几年大家都在讨论在地性问题,但是似乎中国当代艺术领域讨论的在地性依然是以你刚才提及的依循西方的主流叙事进行,欠缺横向对比。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早期实践者来说,民间经验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在地。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在地的叙事中断了,而随着所谓逆全球化的发展,大家又重新开始审视“民间”这个词汇的内涵。
王 欢:
重提“民间 (Folk) ”是我认为有必要将其视为一个连续的范畴来重新理解今天的艺术本体和社会问题,这是我近几年的工作路径。在此之前我们的艺术界有两条路径与之交错,一方面人们使用素人艺术 (naïve art) 、非主流艺术 (Outsider Art) 、原始艺术 (Primitive Art) 以及原生艺术 (Art Brut) 等概念区别于“当代艺术”;另一方面从女巫之锤到东南亚志怪,从民间宗教到个体信仰,从巫术到神话等大量泛神秘主义叙事重新夺回当代艺术的注意力,可以说以上关键词我们都不陌生。

假杂志创刊号《巫术修辞》,主编:王欢,2020
然而,我的学术兴趣既不是过多留恋于什么是/什么不是艺术的本体问题,也不想复魅神秘主义话语,我无法接受将其视为某种艺术创作的“主题”,当代艺术对我来说是一种思想方法,借此让人去理解同时代艺术与文化的角色关系,去理解背后的文化权力和社会问题,那么,我就必须在当代艺术的旁边。所以我事实上并不关心是否是所谓逆全球化的发展让艺术界的人们重新对“民间”的内涵产生兴趣,这是长久以来我自身艺术实践道路的必然选择。是在目睹了众多艺术现场的失望时刻后,才让我意识到我们的艺术有时候离现实太远,才让我想要去知道艺术在成为艺术之前的潜能是什么,我是在大把大把远离艺术的时间里,才发现当代民间现场是一个可以观察当代中国和某些切身问题的入口。

陈花现,《三途世界/桥图/闾山总坛/法索》
“民间自有序”展览现场图片,MACA,2024
摄影:杨灏
Art-Ba-Ba:
你刚才说处在90年代、2000年初的艺术家在遭遇陌生语境时本能性的使用民间经验。这种民间经验实际上根植于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以及知识体系之中,但是我们这一代人 (80、90后) ,基本是在彻底地、激进的城市化、全球化中成长起来的,“民间”反而会让我们觉得陌生,我们和上一代人不一样的地方或许在于,我们真正经历某种文化断裂,从而需要重新寻找并挖掘出一种“民间”。你怎么看待这种差异性?
王 欢:
这需要从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的角度去考虑,很难说因为一代人有特定的成长背景才有处理特定问题的合法性。我的实践不是主动把90年代和2000年初作为参考系,因为即便我们面临和使用的是同一个“民间”语汇,但实际上这个概念的范畴和各自要思辨的对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所面临的现场和语境包括整个社会的进程和艺术的进程也是不可同日而语。那么,这里就有一个不同代际人对各自同时代问题不得不面临的责任问题。
而你提到在你的体感里“民间”叙事中断了,在我有限的田野走访经历里反而觉得那些表面上看似断裂的文化事实上从未中断,它们只是变得隐秘,折叠于社会内部,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的弥散式宗教信仰问题,即便圣象被损毁也仍然有大量群众相信圣象的灵力从未消失。


上图:研究文章《气功画、心灵治疗与身体革命》,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第200期
下图:上世纪90年的气功画,作者:唐文英
Art-Ba-Ba:
相比之下西方也有这种断裂与延续的历史,信仰以某种地下的方式延续,例如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的“三百年教难”。中国的特殊性可能在于其“早熟”的中央集权体制对于“民间”与“官方”两种对抗力量的塑造。比如说当代艺术,你说它对应着国家艺术,甚至对应已经成为固定的历史范畴的传统艺术,都是能够成立的。
王 欢:
我们甚至不需要追溯到那么久远的历史,就以1942年以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为例,显而易见的是治理者对艺术提出了政治诉求,艺术是要为群众和国家形象服务的,符合其艺术立场和艺术选择的就是“好艺术”,相反,当它不符合治理政策时就必然会被打压。对我来说,当代艺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它的思辨性。但对于特定的治理制度来说,任何有思辨性的媒介都有政治上不稳定的风险,这是制度性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能理解什么是国家艺术,什么是民间艺术,要知道,就连“官方”与“民间”二者的表述在“五四”之后都很难再看成是一对反义词了,我们甚至不能用现代观念将民间视为某种“复古”的时间和“折叠”的空间,它只是被放在一个制造的矛盾幻觉之中。放到今天的语境,民间仍然是一个被历史叠加起来的复杂范畴,所以当我们说“民间”的时候,我们要看潜在的语境,是把民间视为一个文化场域,还是社会场域,还是思想领域,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Art-Ba-Ba:
个体性,或主体性,是你关注民间议题的重点吗?这让我想到,对于民间经验的研究在此刻拥有一种现实感,因为我们现在所有人都被扔到了所谓“历史垃圾时间”里,我们需要一些自我疗愈,为自己寻求出路。
王 欢:
我当然非常关心个体性,并且我仍然相信个体的力量可以撬动宏大叙事,但与此同时,这并不是说个体是不具普遍意义的样本。我们完全可以追溯至“五四”以来的遗产,因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影响其实就是对普遍意义上“人民”的改造,将“百姓”概念从附着于治理者和帝国的色彩中解救出来,“人民”才开始逐步强调个体的重量,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人民要觉醒的!是要夺回属于或者说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主体性的。
可以说,五四运动前后人民的概念和我们去想象人民的主体(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巨大改变,那么,人民所构成的民间主体也是发生巨大改变的。民间不再是作为帝国权力的附着领域,著名的知识分子们才将民间视为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领域,去关心乡土社会和民间文化。然而,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这些民间文化是因为文化运动之后才涌现的吗?显然不是,是有太多一直以来本就有的潜力被压抑了,这些压抑的部分因为条件改变而得到解放。民间当然是研究中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范畴,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必须将“民间”视为一个具有鲜活潜能的领域来理解,而不只是一个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文化问题。

张晓,《苦涩嘉年华》,2017-2024
“民间自有序”展览现场图片,MACA,2024
摄影:杨灏
Art-Ba-Ba:
现在讨论民间秩序整个语境变得更加敏感了。这会对你的工作和研究造成什么影响?可能在前几年讨论相对宽松的时候,民间可能只是一种文化资源,但现在,它似乎影射了我们的现实处境,生存空间愈加逼仄,你不得已要以一种很隐晦的方式加以宣泄。
王 欢:
我只能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充分工作,它吸引我的不只是某种与当代艺术语法有差异的美学特质,而是这背后反映出硬生生的现实:人和社会保持怎样的距离活着?和自己的内心保持怎样的距离?又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自洽?我只是知道“民间”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资源,民间是一种处境。
Art-Ba-Ba:
回到你去年的策展“民间自有序”,展览中的创作者拥有各自不同的身份。比如艺术家陆平原,是一位活跃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职业艺术家,他和王玉玺这样的个体显然拥有不同的语境。但从直接的观感上来看,我们基本可以认为王玉玺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更加天然的“民间”色彩。你如何看待你搭建的框架中这些身份迥异的个体?
王 欢:
陆平原和王玉玺当然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艺术世界,但是我们无法用简单的职业或业余这样的话语否定或确立他们各自创作中所展现的质感。同样,像叶甫纳和张晓都是作为职业艺术家,却拥有各自完全不同的民间语境。所以如何在一个中等体量的展览中呈现民间的复杂性?我需要营造的感觉是名单里每一个人的语境都有所不同,却隐隐暗含着某种共性的质感。在最初考究参展名单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展览一定不会是“十个郭凤怡”,或是“十个张晓”,那不是我想要的。我要讨论的,必然要呈现民间的复杂性。至于谁比谁更“民间”并不重要。


上图:“民间自有序”展览现场图片,MACA,2024
摄影:杨灏
下图:王玉玺,《无题》,年份不详
布面水粉
“民间自有序”展览现场图片,MACA,2024
摄影:杨灏


上图:“民间自有序”展览现场图片,MACA,2024
摄影:杨灏
下图:叶甫纳,《中国民间艺术图谱》,2024
布上刺绣,综合材料

《郭凤怡:宇宙经络》,主编:王欢
策划:《普遍》(手册)
联合策划:假杂志、长征空间 ,2024
Art-Ba-Ba:
在展览中,不同的民间最终是不是还是要落在艺术这一点上?
王 欢:
实际上我非常不希望制造的结果是民间文化被当代艺术所征用,而是我认为有必要将民间文化和当代艺术放在更大的尺度里平等看待。这也是之所以在展览中有如此多不同文化背景实践者的原因,而策展所做的事情,除了搭建一个物理的展览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制造艺术的条件。

西亚蝶,《拉手娃娃》《洞》《乐》《巧娘娘》《蝶》《乐》《翔》
“民间自有序”展览现场图片,MACA,2024
摄影:杨灏

周绍江,《Hand in Hand》《无题 编织 No.1》《Voguing Now》
“民间自有序”展览现场图片,MACA,2024
摄影:杨灏
Art-Ba-Ba:
所谓不同路径之间的边界的结构实际上也一直处在变化之中。
王 欢:
的确如此。就像展览中的郭凤怡的一生,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当郭凤怡其名赫然出现在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名单时,国内有着几乎完全不同的两种声音——对“画鬼符”的声讨和“拓展边界”的声援,两方几乎争论到完全不可和解的程度。现在十多年又过去了,似乎更多人接受和正视了郭凤怡的创作。如果以郭凤怡作为尺度,这十年发生了什么?我相信很大程度是当代艺术界某种学术趣味的转移,以及对自我必然的反思。无论语境发生了什么天翻地覆的改变,我们再回看郭凤怡的一生从1989年创作之初直到2010年过世,是她的创作改变了吗?并不是的,尽管我与她素未谋面,但我相信她始终如一,变化是整个艺术的定义在晃动,在摇摆。所以,语境和条件是一个前提。这也很像是我前面提的策展的意义对吧?同样的作品在不同的条件下会激发不同的理解。

“郭凤怡:宇宙经络”,策展人:王欢,长征空间,2023


“郭凤怡:宇宙经络”展览现场,长征空间,2023
Art-Ba-Ba:
“民间自有序”不是一个典型的研究性展览,你如何处理研究和展览的不同语境?
王 欢:
研究型展览和研究型艺术是我近年一直在反思和警惕的问题,在过去十几年里,研究型艺术被大量学术话语需要从而被太多人误会它的本意。也许是因为我作为写作者和策展人的角色与艺术打交道的缘故,我还是坚持认为,当代艺术重要的特质是承担了必要的启蒙和思辨责任,这是艺术进程的必然阶段。出色的思辨性是会闪烁着那个被我们称之为“艺术性”的光的,让人共情的研究从来不会夺取艺术的感性。所以在我近几年的策展实践里,我尽量让研究工作的部分以合适的方式出现,比如论文写作和策展在必要形式上分开,但是会处理相通的问题。我觉得比起是不是看起来“像”研究展来说,真问题更重要一些。


上图:中原田野考察现场,人群围绕“帐盘”展开交流,2017
摄影:张晓
下图:中原田野考察现场,一位“民间画师”在广场展示巨幅“帐画”引来路人围观,2021
摄影:王欢
Art-Ba-Ba:
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你的研究似乎侧重于民间经验中创造性的部分,但民间实际上还隐藏着暴力的因素。如果不提及暴力,会不会有知识精英经常会陷于其中的浪漫化“民间”这一概念的危险?
王 欢:
你提的问题是我留在了研究写作部分处理的,其实展览中古务运动的作品也有所回应:“地下六百年”里的唱经最早是源自于明朝时罗教的教义,被创造之初实际上是通过整合底层群众共同的命运,动员人们参与到民间宗教之中,只是几百年过去了,声音与唱词没有了当年的语境和功能而流变成一种隐秘的文化。
我的研究写作部分暂时使用的副标题就是“秘密社会与艺术自驱力”,这两个词乍一看毫无关系对吗?而我想谈论的就是其中被长久以来忽视的关系。很多学者对秘密社会的研究范畴基本上是通过1949年以前历史上的各种农民起义来追溯一套民间的革命叙事,而我在田野考察过程中发现,秘密结社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因为当代条件不允许这样的“革命”诞生,集结则成为了不具革命条件的即兴冲动与情感慰藉。在这里就有一个硬生生的现实问题:当个体的境况面对现实种种已经无计可施的时候,他怎么与自己和解,与社会和解?那么,对向外改造的诉求开始逐步转向内心,我引用的词汇是“内心的革命”,在这个自我内心改造的技术下,就会有许多精神性、文化性和创造性部分的诞生,我们又如何识别这些在主流艺术和文化话语之外的产物?也就是我所关心的部分。


上图:古务运动,《地下六百年》,2023-2024
“民间自有序”展览现场图片,MACA,2024
摄影:杨灏
下图:古务运动,《大地恓惶》,2023
影像,图中摄影作品为张文心的《歌唱者》 (2023)
Art-Ba-Ba:
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革命动员式的民间往往会走到“民间自有序”的反面,即完全的失序。暴力也由此产生。
王 欢:
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我指的民间自有序是为“天下崩散而民间有序”,是必须从一个更加长远的视角来审视这种连续性:短暂的失序总是在酝酿着新秩序的可能,这是秩序的必然代价。
文章来源:art baba
版权声明:除原创作品外,本平台所使用的文章、图片、视频及音乐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如部分文章或文章部分引用内容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或作者名称及原始出处标注错误等情况,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联系邮箱:236977919@qq.com。发布者:admin,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ystm.com/news/12682.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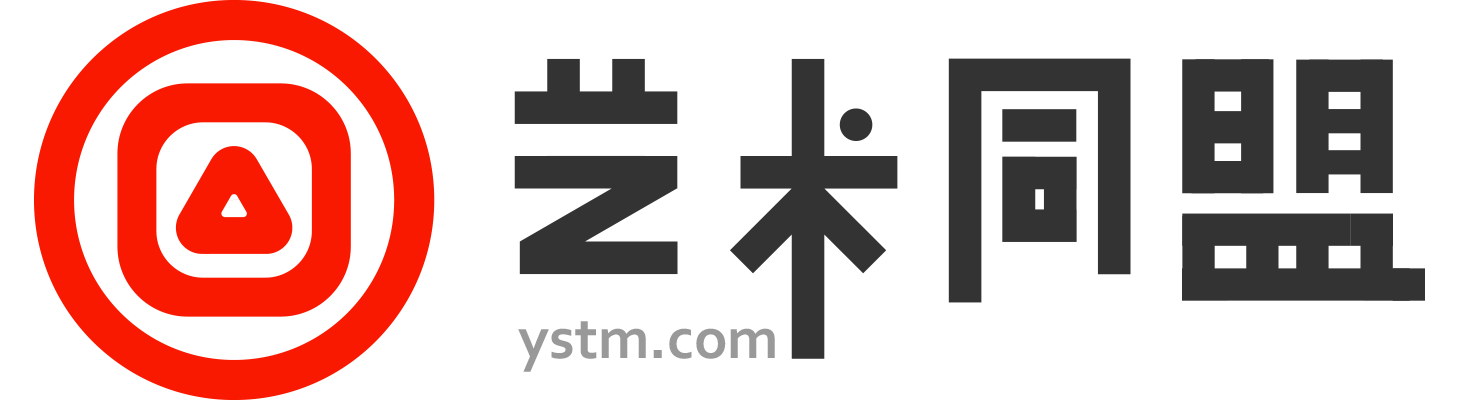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