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艺术中存在阶级意识,那么它应该存在于那些呼吁我们不止步于观看的作品之中。

Sung Tieu, 4710 × 3410萧崇《4710 × 3410》
2023年
萧崇“千次”(One Thousand Times)展览现场,2023年
图片鸣谢温特图尔美术馆
几年前,我写过一本书来探讨艺术语境下的“阶级”主题——这个词很容易被替换成任意一个相关术语或是同义词,比如“不平等”或“剥削”。因此,人们会讶异于我并非天然地关心那些有关苦难或贫穷的描绘。但这并非因为我漠不关心,或是我在试图忽略劳动人民面临的严酷现实;而是因为,对工人阶级的描绘一旦脱离了政治背景,且如果没有指出导致其处境的确切条件的话,这种描绘便会将他们的状况自然化——使之看上去不过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可悲之事。
然而,比这更糟糕的是:近距离地记录工人阶级的生活,然后不道德地把它作为精心设计的避税方案的一部分,出售给高净值人士。所有的艺术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着这个过程,尽管有人很少参与、且不情愿参与,可有些则乐此不疲地让自己的作品沦为物件。后面这类艺术家可能会自我安慰,认为他们在艺术界的存在是有长远意义的,可一旦他们的存在被反复用于政治宣传,用于洗白那些最有权势之人的声誉和良知,那就不再是如此了。这种运作方式是压榨性的,它将艺术家的职业生涯、银行存款和收藏家的野心置于社区的主权之上。它还加深了人们对阶级的错觉,即认为阶级只是一个关于再现的问题,而非结构和经济上的压迫。
近年来,彼得·多依格(Peter Doig)这样的艺术家催生了具象绘画的复兴,其追随者们又进一步推动了它的发展——这表明了艺术向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回归,对眼睛及其同类物那至高无上地位的回归,这和本文所述的趋势脱不了干系。在我看来,创造力应摆脱物质条件束缚的这种论点,一直都是颓废和浅薄的,而且也不甚准确,因为它假定曾有过这种艺术运动,或者说它假定创造力是绝对的,而不是被环境持续重新定义的。当大部分生活为视觉信息和屏幕主导时,完全相信眼睛似乎是危险和糟糕的;更糟糕的是,近年来流行的具象艺术更注重结果(或效果)而非原因,尽管它们有意批判美国消费主义、好莱坞式贪婪和大规模生产,却显得像是在嘲笑劳动人民和他们的欲望。
我想到了伊西·伍德(Issy Wood)和约瑟夫·耶格尔(Joseph Yaeger)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他们创造的后电影式(postcinematic)和广告式的地狱景观极为诱人,但他们的审判也戳痛了在这种现实中长大的我们。《芭比》这部(烂)片在2023年上映之后,我在社交媒体和博客上读到了无数的帖子,它们都讨论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消费者们对塑料制品的需求——“需求”一词轻便地抹去了战后的经济状况,它让欲望变得廉价,使得数十亿人有可能、甚至有必要,退缩到大规模生产和合成产品中去。决定消费的并不是偏好,即便是富人,那些极少因需要而消费的人,也无法想象这样的事情。对于被剥夺了时间、自由和选择权的人们来说,廉价且快速的消费主义是唯一的快乐源泉;而在画廊空间里嘲笑和讥讽这些欲望之物,实在是太轻易、太低级了——把对廉价商品的可怜而不堪的需求,视为一个病态社会持续衰弱的症状?这很轻蔑。

《芭比》(静帧)
2023年
导演:格蕾塔·葛韦格(Greta Gerwig)
© Warner Bros
如果说艺术中存在阶级意识,那么它应该存在于那些呼吁我们不止步于观看的作品之中。这些作品挑战着我们的凝视,使我们质疑那决定着我们命运的权力结构,质疑那些加固了这个不平等系统的艺术家,质疑那些用于异化一部分人、接纳另一部分人的规范。这些作品告诉我们,阶级并不是一种可以被简化为景观的独特现象,而是一种我们在其中生活的机制,它的排列远比一间廉租房或是平顶酒吧的内部结构要复杂得多,它的影响深远,使我们所有人都成为同谋。
这些作品不必拘泥于某种传统或形式,无论是在表演、装置艺术、新唯物主义、极简主义雕塑还是电影等领域,都有许多从业者做出了相关贡献。像皮尔维·塔卡拉(Pilvi Takala)和萧崇(Sung Tieu)这样的艺术家,他们并不太关注刻画和包容的问题,而是更注重挑战社会契约。塔卡拉的作品常常围绕她参与的、各种形式的国家控制和监视展开,它们潜在的荒诞性,在电影的戏谑表演中暴露无遗。《密切监视》(Close Watch, 2022)戏剧性地重现了塔卡拉在一家私人安保公司做卧底时的对话和互动,艺术家及其同伴故作正经的表演风格,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们在公共场所互动时,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歧视。这本无可厚非,也颇为有趣,不过塔卡拉的天才之处在于,她不愿妄加指责,而是聚焦在那些受就业压力所迫的人们面临的道德危机上。没有人愿意被监视,也没有人愿意为安保公司工作,但赚钱的必要使二者成为现实,让原本无辜的人,变为一种与其最深刻信仰相悖的意识形态的同谋。

Pilvi Takala, Close Watch(still)皮尔维·塔卡拉《密切监视》(静帧)2022年,多通道视频装置
图片鸣谢Carlos/Ishikawa,伦敦;Stigter van Doesburg,阿姆斯特丹
在《实习生》(The Trainee, 2008)中,塔卡拉扮演了一名在营销公司实习的研究生。实习期间,塔卡拉进行着她所谓的“脑力劳动”:坐在空荡荡的办公桌前,一连几个小时盯着房间发呆,或者一连几天来回地乘电梯。这引起了同事们的关切甚至是恐惧,其中,男性同事们似乎不仅质疑了她的行为,还将其行为性别化。这是一部关于公司环境中劳动者的电影,这种环境极大限制了人的行为。在她周围,人们漫无目的地盯着屏幕,拨弄着大拇指,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有限,而最重要的,似乎是假装工作——唯一能引起人们警觉的,是塔卡拉以生动且毫无歉意的方式,展现出来的一种自身的无用。
萧崇是一位与之截然不同,但同样富有启示意义的艺术家。她关注那些被剥夺了财产的人,以及那些被困在由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织造的永恒非人之网(dehumanising web)中的人。她目前于温特图尔美术馆(Kunst Museum Winterthur)展出的作品《4710×3410》(2023)由几件长方体雕塑组成,它们和萧崇儿时公寓里家具的体积相当,该公寓位于东德为越南合同工建造的住宅区中。然而,与真正的家具不同的是,这些雕塑千篇一律地用廉价层压木材制成——对于穷人、边缘人和无家可归者来说,这种无常和凑合实用的象征再熟悉不过了。
这件作品的呈现效果冰冷且顽固,就像萧崇其他的装置作品一样,它们不仅反映了如移民局入境检查处或就业中心之类呆板、专业化的残酷环境,而且将那些忍受着此等环境的人们所感到的不安外化了出来。这里的一切都似曾相识,但又稍显异常:一把孤零零的、不带座垫的等候室凳子;一张张无穷无尽的表格,上面没有任何信息,只有一片空白;一些平面图和建筑模型,它们勾勒、构筑着无法正常运行的空间。
现在差异更清晰了吗?一种在从中攫取,一种则悄然参与其中以便更好地进行理解。前者打造了人工制品(artefacts)——我指的是那些了无意义到令人沮丧的物件——并以资本家的所有权方式宣告自己的存在;后者则暗中行动、引发混乱、造成破坏,使得此前的世界面目全非。
萧崇“千次”展览现场,2023年图片鸣谢温特图尔美术馆
我评论艺术,并不是因为我是个唯美主义者(aesthete),或是在周末参观画廊的《Time Out》读者——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且粗糙的说法,但还是值得重申一下,因为我遇到的许多艺术界权贵似乎以为这才是重点。我评论艺术,是因为我知道,要颠覆当前的资本主义体系,就必须重新商议现实。这就是艺术对我的意义所在:艺术不是当前流行的陈词滥调所称的一种自我表达之举,也不是创造力,而是致力于赋予意义的活动领域。现阶段的资本主义是如此抽象,它的魔爪深深扎入了我们的骨子里,支配着我们的梦想和欲望,以至于任何想要挑战它的希望,都得从重新评估我们的每一个假设开始。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我刚刚写了一本关于品位(taste)的书,品位正是资产阶级的当务之急。这是基于充分理由的:那些位居政治中心的人——他们缺乏想象力,不知如何超越那狭隘且反常的、正支配着我们命运的权力关系——着迷于让“善者”而非“恶者”(“善”“恶”是按他们的标准定义的)致富的幼稚问题上。在一个视觉刺激过剩的世界里,这种评价越来越流于表面,“善”被认为体现在一个人与我们的文化和审美情趣的相符程度上。因此,不具备任何理论基础的“好品位”,它作为一种由富人和权势之人全权支配的行为准则,只不过是同化和顺从一类行为的美学面向。
我们不应该盯着画中的人看,而是应该盯着国际艺术阶级(international art class)——正是他们鼓励了这种读取世界的肤浅方式,他们乘飞机游览一个又一个博览会,出于私人展示目的,在世界各地挖掘材料和故事。但是,资本家和阶级压迫制造者的装饰需求(decorative demands),不应左右艺术的走向;要想抵制他们,我们可以同迎合这种需求的艺术家和画廊割席——“我们”在这里指的是我们这些撰写、讨论艺术,并最终判定其批判性价值的人。毕竟,无论是在叙事上还是在环境上,他们行为的代价都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低收入的劳动者,而当恶果不可避免地降临时,后者还将被独自留下,面对最严峻的情形。
文章来源: 艺术世界 ArtReview
版权声明:除原创作品外,本平台所使用的文章、图片、视频及音乐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如部分文章或文章部分引用内容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或作者名称及原始出处标注错误等情况,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联系邮箱:236977919@qq.com。发布者:admin,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ystm.com/news/5022.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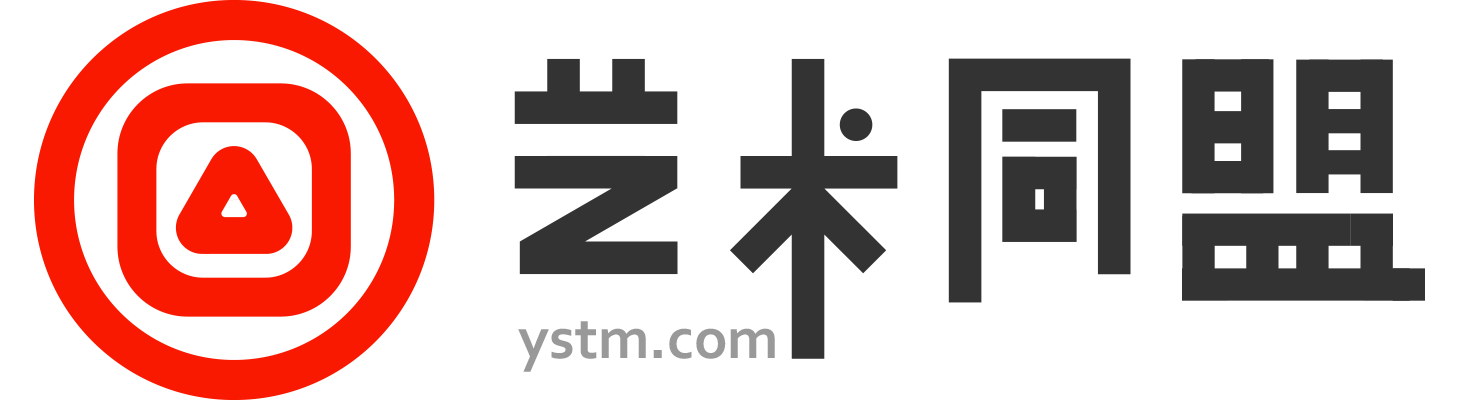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